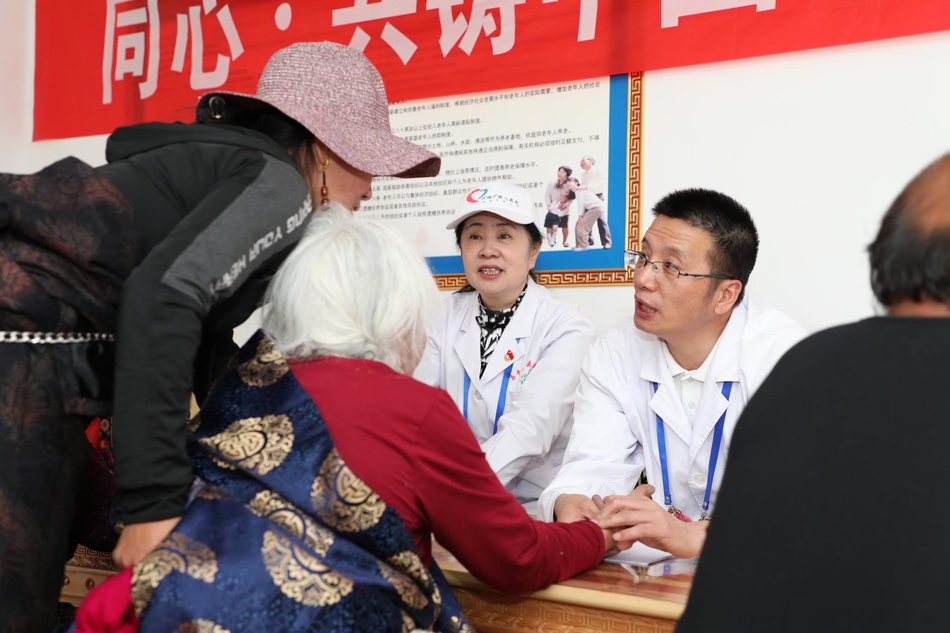人物光影
人物檔案
性 別:男
籍 貫:四川
職務:
“中國電影基金會”----理事
“中國電影家協會”----理事、名譽理事

“中國社會經濟文化交流協會”----顧問
“中國老年書畫研究會”----顧問
“中國書畫收藏家協會”----顧問
“北京華夏文化藝術海外聯誼會”----名譽會長
“北京藝術文化交流中心”----顧問
“湖北荊門市人民政府”----藝術顧問
“廣州萬泉河國際旅遊度假村”----終生高級顧問
成長故事
熱鬧報子街41號
1917年,北京,出生才三天的淩子風,由母親抱著,走進了陽光明媚的院子。
母親抱著淩子風,走出臥室,眉宇間顯露出非常滿足和得意的神色。這是淩家大宅的第一個男孩子;是報子街41號的主人――這位清王朝考場監考官的長孫。
這一天,報子街41號熱鬧得像趕集,前來道喜的、送禮、送錢的人,像串龍燈一樣地進進出出。一片喜氣盈盈,笑語聲聲。母親更是樂得抿不攏嘴,一個老實巴交的傳統婦人總算是為淩家完成了一件非常神聖的事―――傳宗接代。
淩子風出生地報子街41號,是他祖父的官邸。在報子街上,這41號可稱得上是十分有氣派的“小皇宮”,左鄰右舍們都知道,這41號是晚清“做官人家”住的。
祖父的官邸是一座三進的深宅大院,大門外的兩邊有兩座漢白玉大理石的“上馬石”。這兩座“上馬石”很高很大,是兩層的石頭階梯。祖父出門騎馬或坐轎車,都要由差人攙扶著,踩在單腿下跪的差人腿上,然後再蹬上馬或是坐進轎車裏去。
報子街41號的大門又大又高又厚,門上有兩隻大銅環。來客人叫門就要拍門上的環,來客哪怕是輕輕地拍,門鈴也會發出一陣“叮叮咚咚”的悅耳的響聲。大門裏有一間門房,門房裏住著專管開門、關門的男傭。家裏來了客人,男傭得先把客人請到外院的客廳,然後男傭再去向祖父上報。外院和裏院是嚴密地隔離的。
進得大門,迎門是一堵很大的雕花磚的“迎客壁”,迎客壁前放著一隻很大的荷花缸。這隻大荷花缸足足有半個大人高,反正小孩哪怕是踮起腳尖也是看不見裏麵的金魚的。看不見金魚,則是看荷花,從大荷花缸裏長出來的兩朵紅、白大荷花倒是十分迷人的。
大門,也可以說“頭道門”,進得大門後,便是“二道門”了。家中的二道門也是大而好看的。它和普通的門不同,不僅寬大,而且漆著綠色的油漆,綠漆上布滿了一塊塊金色的斑點,據說這種斑點稱作為“撒金”,是用一種很薄的金箔粘在漆麵上去的,顯得富麗、漂亮。進得二門,裏院顯得很大,滿院的磚墁地,隻有在兩棵垂柳下的地麵上顯露出一小塊泥地。
報子街41號的大宅內,還有三道門,這三道門內卻是女傭和馬夫住的。
大院子裏的垂柳揚花三載,淩子風也長到了三歲。他開始在院子裏玩耍起來。他喜歡騎在高高的門檻上,手拿著自己做的鞭兒,嘴裏念念有詞,他是將高高的門檻當起馬來騎了。
搬到外婆那裏去住了
在淩子風的眼裏,奶奶是一個可親可愛的人,但生活的重壓已使她喘不過氣來了―――奶奶終於去世了。她甩下了小孫子而去了;她甩下了報子街41號僅有的一小塊小院子而去了;奶奶實在是太累了。
淩子風哭得好傷心啊。
奶奶去世以後,淩子風和她的媽媽一起搬到了外婆那裏去住了。外婆住在靠城牆根的西柳樹井3號。
外婆家也是有錢人出身。聽“馬大大”說,他的外公祖籍是河南人,是開“騾馬大店”的。這個騾馬大店有很大的院子―――除了客房外,還有供各地往京城運貨的車輛停放的場所、喂養牲口的馬圈,以及堆積如山的草料,當然還有供客商吃飯飲酒的地方。
媽媽是這樣的大戶人家的獨生女兒,是有錢的外公的掌上明珠。成天就在家裏和小狗、小貓玩,要不就是學學繡花,但就是不識字。外公、外婆將媽媽嫁給做官人家的孩子當媳婦,當然是樂意的。
在晚年淩子風的記憶中,西柳樹井3號的外婆家有幾棵比房子還高的果樹:石榴樹、杏樹、棗樹。每年,每當果子成熟的時候,媽媽、外婆就領著淩子風,在院子裏打果子吃,一顆顆果子紛紛打在媽媽、外婆和淩子風的頭上,大家嘻笑著、采擷著,隻是一會兒的工夫,就裝滿了一籃子、一銅盆,淩子風捧著一大盆、一大籃的紅棗、杏子,有多開心啊。
可是有一天,西柳樹井3號的大門口,掛起了一長串、一長串白色的紙錢,在一陣緊一陣的秋風中索索發抖……這是外婆死了。
好人怎麽都會死呢?一會兒是祖父、一會兒是祖母,現在又是外婆。
祖母死了,外婆死了,那誰來陪淩子風玩呢?
淩子風上學了,他有了自己的同學。但他常常逃學,和他的小夥伴一起去爬高高的城牆,多危險啊!要是讓家裏的人知道了,非得挨一頓揍不可。但他們全然不顧,他和他的同學們一起,下河摸魚、上樹捉“知了”,直到天快黑了,他們才沿著高高的城牆摸上又爬下,坐在高高的城牆上,看著自己一天的戰利品:瓶子裏裝著小魚;蘆葦杆上拴著紅蜻蜓、黃蜻蜓,還有一些不知名兒的小花;籠子裏的“蛐蛐”總是少不了的。等他坐在高高的城牆上欣賞夠了,才戀戀不舍地離開城牆,摸著黑,悄悄地溜進了家門。
母親是不知道淩子風又逃學了,隻是見他回來得晚了,身上又是髒巴巴的,少不了幾聲埋怨。
淩子風老老實實地吃了飯,擦洗了,上了床。
看戲看上了癮
一輛擦得鋥亮的黃包車,停在淩子風的家門口。
“馬大大”見到非常熟悉的黃包車,朝院子裏一聲喊:“三兒,接你來了!”
“唉,來啦!”淩子風三步並作兩步,奔出了堂屋。
這是“幹爸爸”差人來接淩子風看戲去的。幹爸爸對淩子風喜愛有加,三日兩頭接淩子風去他的“哈兒飛戲園”看戲……
連淩子風也弄不清楚,從什麽時候起,他成了人家的幹兒子。
這位幹爸爸是離他家不遠的一個名叫“哈兒飛戲園”的老板,這戲園先前是一家武術館,名叫“奉天會館”。現在改成了一家演戲的戲園子。
在哈兒飛戲園,少年淩子風最喜歡的是武醜的戲和花臉的戲。他欣賞的是武醜戲的功夫和花臉戲的臉譜。武功演員站在高高摞起的兩張八仙桌上,一個斤鬥翻下來,輕盈著地,其瀟灑利落的動作,猶如一隻騰空而下的鷹,令淩子風歎為觀止。
除了武功的戲外,淩子風還喜歡畫京劇的臉譜,那一張張各具特色的臉譜,在淩子風看來就是一幅幅精美的藝術作品。
“幹兒子”淩子風在“哈兒飛戲園”看戲看上癮,從此以後,他除了一邊在“哈兒飛”看戲外,還常常約小夥伴們一起跑天橋,跑“廣和樓”,為了看戲,他還學會了瞞著家長逃學。
每天早晨,媽媽照例會給淩子風一些零花錢,以便讓他在肚子餓的時候,買點點心吃吃,媽媽也根本沒有理由去懷疑他會逃學。淩子風拿著這些媽媽給的零花錢,加上他平日積蓄的錢,夠他去天橋、去前門的廣和樓消費一整天了。
早晨,他很聽話地背著書包出門了;黃昏,他看完了下午的戲,正好是學校放學的時候,規規矩矩地回到家裏,然後就吃晚飯,誰也不會去懷疑他這一天沒有去上學。為了看戲,瞞過了媽媽的淩子風,依然是一個聽話的孩子的樣子。
淩子風常去天橋、廣和樓。在廣和樓戲園,他還認識了一個也是愛好京劇的同學,這位同學成立了一個戲友組織,名叫“歆石社”,由於歆石社的關係,久而久之,淩子風居然和廣和樓的科班“富連成”的那些演員們混熟了,例如科班“世”字輩和“盛”字輩的演員中的葉盛章(富連成科班班主任葉春善的兒子)、袁世海、李盛藻、劉盛蓮、裘盛戎等。袁世海還為他畫過一幅京劇臉譜的扇麵子呢。
在廣和樓的一天裏,淩子風除了看戲,就是啊呀呀地唱戲,餓了,就在戲園子裏的豆腐腦攤上買點餛飩和豆腐腦吃吃。淩子風的嗓門在同學中是數一數二的,唱起戲來也像是那麽一回事。
要去師傅那裏練武術
小學五六年級的時候,淩子風拜過一個練武術的師傅。每天放學回家之前,他都要去他的師傅那裏練拳腳、練大刀。他為什麽要去練武術?是他自己要去的,還是他的家人要他去學的?這就不得而知了。抑或是當時舊北京的時尚吧!
這個武術師傅在淩子風的心目中,還是一個有本事的人。五十多歲,人很瘦,但他的筋骨奇好,他挑水,從不用扁擔,雙手一提就上路了,從井邊到家門口可以一直不歇腳。
這位武功師傅平日裏走街穿巷,擔著一個小貨擔,做些鋸碗、補金之類的手藝活,用以糊口。
跟著這位師傅的總共有六個人,都是一些大人,唯有淩子風一人是一個小不丁點的小孩。
白天,師傅去做買賣;晚上,就教他們習武。不論是刮風下雨,還是天氣晴朗,他們在師傅的帶領下,春夏秋冬,練武從不間斷。那一年的冬天,天在下雪,他們卻光著膀子在那裏練呀練的,渾身上下還滿是汗水呢!
淩子風的五位師兄大都住在南城,還有的住在牛街,和淩子風回家不是一路。散夥的時候各走各的。淩子風回家的路要經過西城的太平湖,這個太平湖是一個死水湖,每年夏季下大雨,周邊的雨水嘩嘩地盡往太平湖中流。每到這個時候也是周邊的老百姓和小孩子們最為高興的時候,他們一個個往水中跳,方圓幾十裏,這個太平湖是最為理想的遊泳之處了。但也是在這個太平湖裏,每年都要淹死幾個人。
有人說,太平湖中有“屈死鬼”,每到晚上,太平湖邊有“鬼影”閃動。太平湖雖說是在城內,但也是城中最為偏僻的地方,加上在周圍的老百姓中有此傳說,一到晚上,就很少有人在太平湖邊走動了。
有關太平湖的傳說,還不止這些。在太平湖的北邊,有一株古槐樹,這株古槐樹兩三人還合抱不過來;在這株老槐樹邊有一口枯井,這口井也是一口充滿著古怪傳說的恐怖之井。有人說,每到晚上,在這口井中還會傳出人的哭聲來……
恐怖的“鬼哭”“鬼影”,太平湖成為可怖之湖。
但每天當淩子風練完武功之後,又是偏偏要走這條路,不走這條路,他可要繞一個大圈,走一段很長的冤枉路。
太平湖邊的路,淩子風每天走;每天走,卻沒有發生什麽事,他也沒有聽到傳說中的井中哭聲,漸漸地,他的膽子也越來越大了。
後來的幾天,淩子風故意地在井邊停下腳步,朝井裏張望,聽聽井裏到底有沒有哭聲,結果當然是與傳說相反的。
膽子越來越大起來的淩子風,有時還往井裏扔扔石頭。
淩子風敢於夜走太平湖―――況且是一個十二三歲的少年,在師兄們中間傳為美談,鄰裏們也大大的誇讚淩子風。
淩子風的母親則更是得意,逢人便說:“沒點膽量誰敢?我這小子真行!”
決心去報考航空學校
上中學了,淩子風做起了航空夢―――他想有一天,他會駕駛著飛機,飛上猶如海洋般的天空中去。
淩子風的航空夢,多半是受他的中學時代的同學王凱的影響。王凱是他中學時代的一位好友,他是一位航模愛好者,家裏也有許多航空雜誌和航空方麵的書籍,淩子風常到王凱的家裏去,那些花花綠綠的航空雜誌也吸引了淩子風,引起了他的興趣;有的時候家裏的雜誌還不夠看,他倆就結伴到航空署街的“航空公署”去看。
淩子風向王凱提議:由他們自己買些材料來動手做航模飛機。他的提議一出,立即得到了王凱的響應,於是,他倆從街上買來了木頭、刀、鋸、膠水、沙紙等材料,在王凱的家裏“劈裏啪啦”地幹開了,像一個木工工場,弄得滿屋滿地的全是木屑與碎木塊。
兩位中學生的手工真不比專業的差到哪裏去,飛機各部位的比例都十分的精確、到位,在飛機的各個應該活動的部位,如螺旋槳、機輪、機尾等,他們都做了活動的關節,做得像真的一樣。他們還在機身上塗上了銀灰色。
航模飛機做成了,他們拿到照相館裏去給飛機照了一張相,然後,他倆又騎上自行車到航空署去給署裏的官員們看,這些專業的官員們對這兩位中學生的創造性勞動給予了極大的肯定,他們十分驚訝兩位年紀小小的中學生居然能做出這麽精細逼真的飛機模型來。
製作航模的興趣,又大大地激發了這兩位好友去報考航空學校的決心,淩子風和王凱背著父母去報考了當時在北京招生的杭州天竺航空學校。
王凱的父親知道了兒子去報考了航空學校,並沒有表現出反對的意思,他隻是問淩子風:“你的父親知道你報考航空學校嗎?他老人家支持嗎?”“我還沒有來得及告訴我家父母。”淩子風說。“那你一定得告訴你的父母才對,一定要去告訴他們的。”
淩子風的母親聽後並沒表現出反對的意思。
晚飯後,大姐對淩子風說:“媽叫你到西屋去一趟。”
淩子風去了西屋,路經父親的屋前,隻見老人家桌前的台燈亮著,也不跟他說什麽。到了西屋,母親在忙著整理床鋪,對淩子風說:“今天你就睡西屋吧,考學校的事,早上你爸爸再跟你談,不早了,你先睡吧。”說完,母親走了,臨走的時候,她還幫兒子關上了門。
淩子風隻是不明白,為什麽讓他睡在西屋。他迷迷糊糊地進入了夢鄉,睡夢中,好像聽見父母倆在低聲說話。
天亮了,淩子風從紙窗的破洞處朝外望,他大吃一驚:門被反鎖了,呀,他被父親關了禁閉!
父親走了過來,他挾著一隻布包,拎著雨傘。他站在門外叫兒子,冷冷地對他說:“我反對你去報考航空學校,航空很危險,淨死人。”
淩子風用絕食來抗議父親的反對。
幾天時間過去了,前來招生的天竺航校的人也回去了。淩子風的鬥爭徹底失敗了,他哭得好傷心啊。從此,淩子風大門也不出,學校裏也不去,他怕見著王凱。
演藝經曆
隻有一句台詞的角色
後來成為我國著名話劇與電影表演藝術家的藍馬,拉淩子風一起參加“美美劇社”的劇藝活動,淩子風就參加了。
“美美劇社”是北京美專的一個學生藝術劇社。
藍馬是這個學生藝術團體的骨幹,他又是淩子風在這所學校的同班同學。藍馬畫畫並不怎麽樣,但他愛好演戲。照淩子風的話說,“藍馬不好好地畫畫,但是他演戲卻是很好的”。
藍馬在這個學生劇社裏是個活躍分子,就像他竭力鼓動石揮參加話劇團體“明日劇社”一樣,他也鼓動淩子風一起演戲。淩子風在晚年回憶起這段曆史的時候,很看重在“美美劇社”的活動,他說,他日後從事戲劇活動,是從“美美劇社”開始的。
淩子風參加了“美美劇社”的第一次演出。
分配給他一個隻有一句台詞的角色―――聽差的;而藍馬演“老爺”。“聽差的”手捧一件衣服給“老爺”送去:“老爺,衣服洗好了!”就是這麽簡單的一句話。
可是,當淩子風一上場看到台下密密麻麻的觀眾時,心裏一下子就慌了,心裏一慌,就連這麽簡單的一句台詞也給徹底忘了。淩子風愣在那裏一下子不知道說什麽好。
還是藍馬有經驗,他見淩子風沒詞了,立即接上去說:“送衣服來啦,放那兒出去吧。”
藍馬一句話,把淩子風給救了。
這是淩子風有生以來第一次演戲。
離開家人的日子確實是太苦了,淩子風常常是沒有飯吃。
在美專的時候,學校裏有一個“三c畫會”的美術組織,是由張仃、荊林、陳誌高三人組成的。這幾位都是他的好友,有時候,他們開一個畫展,張仃賣掉兩幅畫,就可以一起混吃幾頓;荊林是山西人,家裏有的時候還寄一些錢來,淩子風也可以仰仗著,吃上一兩天。但總不能老吃別人的呀!
沒錢了,沒吃了,淩子風就去倒別人的“筆筒”。平日裏,人家將一二個小錢,丟在筆筒裏,時間一長也給忘了,從筆筒裏倒出一二個銅板來,就又可以去換幾個窩窩頭吃了。
在美專四年,淩子風和張仃算是最為要好的同學和朋友了。
張仃是從東北流亡到北京的學生,也很窮。不知為什麽,淩子風就特別喜歡這個平日裏剃平頭、穿一身藍布大褂的小個子張仃,也許是淩子風看張仃的畫畫得特別好吧;張仃對淩子風也有好感。
有一天,在學校的門口,他倆碰到了,張仃就對淩子風說:“淩飛,你的畫畫得太好了,我們交個朋友吧?”
淩子風也有這個想法,“好!”他一口應諾。
說著,兩人“撲通”一下都給對方跪下了,算是交了結拜兄弟了,他們的這一舉動,倒是引來了好多驚訝與好奇的目光。
他決意再度南下
其實,在淩子風的眼光中,王大化比自己還要“瘋”―――
淩子風清楚地記得,“八ⷤ𘀤€日本宣告投降的那天晚上,淩子風正在魯藝後院一排教職員宿舍的平房裏看書,忽然平地一聲驚雷,從外麵傳來一陣響過一陣的喊叫聲,長號、鞭炮、鑼鼓也一齊響了起來,像山洪暴發,像土窯倒塌,淩子風一下子驚呆了。
淩子風站起身向門外走去,還沒有等他走到門口,王大化一下子推開門,從外麵衝了進來,大叫著:“哥,小日本投降了,鬼子投降了!”說著,一下子撕開了淩子風身上的襯衫,抱倒淩子風,又是叫,又是滾。叫夠了,滾夠了,又把自己身上的襯衫也一條一條地撕下來,還一把抱起淩子風床上的被子衝出門去。
門外是另一個世界:一個狂歡的海洋,一個沸騰的人潮。
魯藝所有的鑼鼓都敲響了。人們臂挽著臂,排成一列列的長隊,在魯藝的大院裏踩著鑼鼓的點子,跳著,唱著,腳步震響著大地……
突然間,王大化用長杆高擎著燃燒的棉被衝進了人流,世界上最大的火炬在沸騰的人流中跳躍著、飛舞著,人群頓時歡呼起來。
(在北京美專的時候,淩子風的一條被子送去當鋪換錢去看了蘇聯電影;如今這條被子卻被人們的熱情之火燒了!)
興奮的人流將魯藝的院長周揚高高地舉起,舉到人流的前列,人流環轉著,不停地環轉著!
延安的老鄉也樂瘋了:魯藝門前的一家麵館老板對著沸騰的人群大叫著:“吃麵啊,不要錢!”新市場賣沙果的老鄉把一筐筐的沙果倒在地上,一個勁地大喊著“吃沙果了,不要錢!”
山頂上,一簇簇的篝火燒了起來,山上山下,秧歌隊舞了起來。在這狂歡的延安之夜,淩子風和王大化瘋在一起了。
日本投降後,魯藝組織了華北工作隊和東北工作隊。淩子風去了華北,王大化去了東北。此次分別,不幸卻成了他與王大化的永別。
王大化在東北乘卡車的時候,由於過早跳車,不幸車禍喪生!
淩子風渴望從事藝術之心不死。
在濟南姐夫李苦禪、大姐淩成竹的家裏,他十分留戀北京美專的讀書生活,他也很想念那些和他同窗過的同學們。
淩子風在報紙上看到了南京國立劇專的招生布告,他決意再度南下,去南京!去報考當時在國內享有盛名、一流戲劇名流薈萃的名校。他愛好美術、且在北京美專專門學過美術、雕塑等專業,南京國立戲專也有戲劇美術係,他可以在那裏繼續得到深造。
給他單獨開了考場
南下決心已定,大姐淩成竹和姐夫李苦禪十分讚同淩子風去報考,並給了他五元錢作為盤纏和生活費。
到了南京,淩子風就急急地奔向學校,但令他失望的是,學校的招生已經結束了,考生們已經在翹首盼望著揭榜了。這怎麽辦?
淩子風抱著試一試的心理,央求校方給予自己一次補考的機會。當時學校的校長是餘上沅;曹禺是該校的資深教授。前輩們見淩子風求學心切,又考慮到他是北京美專的畢業生,決定給他單獨開了考場。
餘上沅、曹禺兩位大考官又是提問,又是看淩子風的美術作品,兩位大師一致認為:眼前的這位學生是一位“可造之才”,決定給予破格的錄取。
入學南京國立劇專是淩子風藝術道路的一個轉折點。
如果說,在此之前淩子風還處在藝術的學習階段的話,那麽,進入國立劇專他不僅有了更為廣闊的學習領域,而且在藝術上有了更多的實踐機會:大師們就在他的身邊!他可以在大師們的直接教誨下,在藝術的殿堂裏得到深造。
淩子風的美術專長在劇專得到了進一步的發揮。學校裏牆報、校刊上的漫畫多半出於他的手筆;師生排戲的布景也是出於淩子風之手。令淩子風感到驕傲的、也可以說應該載入他個人藝術史冊的是:校長餘上沅導演的莎士比亞的名劇《威尼斯商人》、曹禺的名劇《日出》,其中的舞台美術均是出於淩子風之手。
淩子風的這兩劇的創作給他帶來了名利雙收。僅《日出》一劇的美術布景創作給了淩子風200元的稿酬。這個數字對一個學生來說是很可觀的。淩子風拿出其中的一半給母親寄去了。其餘的給自己作生活費,是很富裕的了。
想起他剛進劇專的時候,經濟上是十分拮據的。姐姐給的五元盤纏錢很快就花完了,吃飯也成了問題。幸虧和淩子風同宿舍住的一些同學,如李增援(後參加新四軍,著名歌曲《麻雀燒餅》的作者)、胡子(上海人民藝術劇院導演、舞台美術家)、黃若海(電影編劇),還有俞世龍、辛子萍等,對淩子風都很好,知道他沒錢吃飯,都給他出主意:讓他一起參加吃包飯。
包飯,即四個人一桌,一個月是四元錢。每天總有不來的同學,也就是四個人中總有缺席的人。淩子風就在缺席的一桌中混飯吃。這樣,淩子風一連混了好多日子。
淩子風愛熱鬧,愛說笑話,他到哪一桌,哪一桌上就是笑聲不斷。時間一長,他吃白食的身份也就暴露了出來。
第一部自己的作品
《獄》是一出獨幕劇,也是淩子風在南京國立劇專念書時代的第一部自編、自導、自演的作品。在四麵均是高牆的獄中,一群渴望自由的牢友在呼喊、在掙紮;一縷陽光從高高的小窗裏射進來……這是一曲爭取自由、渴望自由的呼聲。
《獄》也是淩子風所處那個黑暗的年代裏從心底發出的呼聲;也許就是他本人十個月的獄中生活的寫照。
校長餘上沅與名教授曹禺對這一出戲很是欣賞。餘上沅還想將此劇作為學校的保留節目,供以後公演。而曹禺則認為劇中的哭聲如果改為女聲的哭聲則更為淒涼和更為令人同情。
相反,這一出戲則驚動了國民黨的文化特務張道藩。
在一個例行的星期一“總理紀念日”早會上,張道藩以這個學校校務委員會主任的名義向全校的師生訓話,他出人意外地卻拿淩子風來示眾:
“淩頌強,站出來!”
在密集的同學座位中,淩子風高高的個子站了起來。
“大家都看看他!這不是一個好學生,你們大家都看到了他編的那個《獄》麽,這不是一個好劇,但是居然還有人說它好,好在什麽地方?他已經引起了有關方麵的注意,你們要小心,不要接近他!”
獨幕劇《獄》給張道藩要開除淩子風提供了口實。這給校長餘上沅出了難題。淩子風是學校裏的高材生,這樣的學生他是從心底裏不願意開除的,但是不照張道藩的指令做,這不是有意與張作對嗎?
校董事會終於作出了開除淩子風的決定。那天全校的師生都集中在學校的大禮堂裏,當校長餘上沅宣布開除淩子風的決定後,會場下麵開始騷動了起來。
首先是教師王家齊從座位上站了起來,他反對開除像淩子風這樣的好學生,緊接著,他列舉了淩子風在平日裏的表現:一年四季為全校的師生刻蠟紙、印講義、編劇本、畫舞台布景、製作道具、看管倉庫……反正,淩子風在許多方麵都是一個不可多得的好學生,而且是一個有才華的好學生,因此,開除這樣的學生是完全沒有理由的。
王家齊的發言剛過,學生冼群也站出來力陳淩子風的好處,竭力說服校方挽留淩子風。
兩位發言一個接一個。忽然,會場上有學生站出來大聲喊:“如果校方不收回開除淩子風的成命,我們全體就站在這裏不走了!”
這位學生的一聲喊,全體師生竟嘩啦一下全站了起來。平靜的大禮堂裏像刮過一場風暴。
淩子風看到這一場麵,眼淚一下子掉了下來……
大禮堂裏的氣氛由一個開除淩子風的會,轉變成了為淩子風說情的會、評功擺好的會。
本來就不想開除淩子風的開明校長餘上沅,這下子有了順水推舟的口實,他對全體師生說:“開除淩子風是校董事會的決定,我一個人無權改變。”但他表示要把情況帶到校董事會上再去討論。
幾天之後,開除的布告換成了處分的布告:留校察看。
人物年表
1933年北平美術學院雕塑係學習。
1935年南京國立戲劇學校第一期生,舞台美術係學習。
1937年武漢中國電影製片廠美工師。
1938年抗日藝術隊文學部部長,西北戰地服務團團委、編導委委員,晉察冀邊區劇協常委、鄉村藝術輔導、鄉村藝術幹部訓練班校長。
1940年冀中軍區火線劇社副社長。
1944年延安魯迅藝術學校教員;年在魯迅藝術學院塑鑄“毛主席像章”向中共七大獻禮。
1945年華北聯大藝術學院教員。
1946年延安電影廠演員、延安戰地攝影隊隊長、西北電影工學隊教學部部長。
1947年石家莊市委宣傳部聯絡員、石家莊電影戲劇音樂工作委員會主任、石家莊電影院總經理,並寫了《接收。改造。管理城市電影院經驗總結》報中央。
1949年東北電影廠導演,北京電影廠導演。
感情生活
青年藝術家到了戀愛的年齡。那年,淩子風21歲,少女18歲。她是一位生在中國的法國少女,她的中國名字叫周幗芳。
周幗芳這個名字是誰為她起的?又為什麽姓周名幗芳?淩子風沒有去問她。也許,她的這位法國父親以為周是中國的大姓,而“巾國”之“芳”對女孩子來說又是一個非常吉利的詞吧!
周幗芳的父親是一個很有錢的生意人。他長期在中國經商,福建、廣州、汕頭等地他都擁有洋行;她的一位叔叔也在中國經商。淩子風和周幗芳戀愛的時候,她的父母已經去世了,她的叔叔成了周幗芳的監護人。
淩子風與周幗芳相識,是因為他們倆都在南京讀書,有機會經常在一起:學生會、同樂會、遊藝會……各種各樣的學生團體活動,使小小的石頭城的學生們常有機會聚合在一起。
當時淩子風是著名的國立劇專的文藝活動分子;周幗芳在南京匯文中學念書,兩個學校的文藝骨幹又常常能在一起排戲,淩子風又能給他們充當導演。淩子風和周幗芳就是通過兩個學校的文藝交往相識了。擔當學生藝術活動導演的淩子風很自然在學生文藝骨幹的心目中,是一位才子。
淩子風清楚地記得,那時候,他給匯文中學排演《九一八之夜》。這個戲周幗芳沒有參加,因為她是一個“高鼻子、藍眼睛”,不適合演一個中國人。她於是就在一邊看他們排演,同學們都看得出,周幗芳在追淩子風,而且是追得很凶,很主動,這是一個公開的秘密,大家都心照不宣罷了。
淩子風和周幗芳相識後,兩人經常一起出去玩:上館子吃飯、上戲院看戲、上公園、逛馬路……兩人常在一起,好不開心!
但這一切的費用開銷,全是由周幗芳掏錢,因為她有錢;而淩子風則是窮學生一個!
周幗芳還送給淩子風一張她自己的肖像照片,底色發黃了,但被塗上了彩色。背麵寫著:“給親愛的……”在淩子風看來,這當然是周幗芳送給他的定情物了。
據淩子風的回憶,周幗芳的父親在廬山有一幢別墅。別墅很美,有花園草坪、有網球場。熱戀淩子風的周幗芳曾約淩子風去廬山別墅整整玩了一個星期。當時他們都很年輕,在愛情問題上也很守規矩,一周內,雖然在一起玩,同睡在一個屋簷下,但沒有擁抱,也沒有接吻,真是廬山上的一對純情少男少女!
熱情的周小姐對前景充滿了幻想。她曾動員淩子風與她同去美國,將來再一起回中國,開一家最大的影劇場。
但淩子風似乎對周小姐的這一邀請並沒有動心。年輕、熱情的淩子風此時有他自己的追求。當時,他受到兩個方麵的影響:一是她的大姐在延安,她來信鼓勵淩子風去延安;二是淩子風年輕的時候看了不少蘇聯進步的小說,如《母親》《大學私生活》等,也向往去延安。
在這多種因素之下,淩子風與周幗芳的愛情就不可能再有繼續下去的可能了。
晚年三夢
淩子風的晚年三夢,是指他夢寐以求想拍的三部片子:《天橋》、《李白》、《弘一法師》。多年來,他一直在想著這三部片子能夠有朝一日化為他的現實。
三夢之中,《天橋》算是排行第一,也是老頭做得時間最為長久、用心良苦的一個夢。隨著北京市政建設的擴展,具有民族特色的北京天橋已經蕩然無存,這一自清末以來,一直是民間藝人獻藝獻技的“雜八地”,早已成為曆史的舊跡。在老北京的心目中,天橋一直是他們的心儀所在,是他們常常眷念的地方。
淩子風的“天橋”夢,不僅是指拍一部長達五十集的電視片、一部電影、一部天橋專題片,他還想在北京的市郊重建一個“天橋”。
淩子風夢想重建的天橋,在北京的近郊―――靠近北京機場的順義縣天竺鎮。他用了一年多的時間,跑地皮、談資金、打報告。他理想中的天橋不是布置式的天橋,而是實實在在的真天橋。在這裏,將有一萬多名職工在天橋裏從事各種各樣的行業,有飲食業、有服務業,也有各色各樣的藝人……在街道上有舊式的有軌電車,有五星、四星級不等的中國四合院式的賓館。要讓來中國的外國友人,一下飛機就想參觀“北京第一鎮”,並在那裏住下。當然,他們還可以在那裏觀看淩子風的作品《天橋》。
淩子風說,《天橋》的影片可以向世界各國介紹,文獻資料片可以提供給各國大學的圖書館,以學習天橋曆史之用。
淩子風晚年的第二夢,是想把我國曆史上的大詩人李白搬上銀幕。李白,才華橫溢,性格豪爽,淩子風深為崇敬。他覺得自己在許多方麵類同李白,拍李白的傳記片也是為了抒發他個人的情懷。
想在有生之年完成的第三個夢,則是他渴望將弘一法師李叔同的生平搬上電影。李叔同是我國清末民初的一個大藝術教育家,早年東渡日本,學習西洋繪畫,他的才華涉及多方麵:音樂、戲劇、教育等等。而且,他個人的曆史富有極強烈的傳奇色彩。這諸多方麵是吸引他想拍李叔同傳記片的起因。
淩子風說,如果在他的有生之年,這三個夢能夠得以實現,那麽,他這一輩子的電影生涯也可以劃上一個圓滿的句號了。
主要作品
擔任導演的影片
《光榮人家》《陝北牧歌》《金銀灘》《春風吹到諾敏河》《母親》《深山裏的菊花》《紅旗譜》《春雷》《草原雄鷹》《楊乃武與小白菜》《李四光》等。
擔任演員的影片
《勞動英雄》飾主角角勞動英雄(46年,延安電影廠)。
攝影作品
拍攝的保衛延安戰地紀錄片被編入《紅旗漫卷西風》;
拍攝了毛主席在延安指揮全國戰場看地圖的著名照片。
擔任編導的戲劇
《獄》獨幕劇(35年)、《日本的五月祭》(38年)、《人間地獄》(38 年)、《哈娜蔻》(38年)及導演了陳荒煤編劇的《糧食》。
擔任演員的戲劇
《國民公敵》飾主角司多門醫生、《日出》飾黑三、《保衛我們的土地》飾姐夫、《八百壯士》飾一壯士、《熱血忠魂》飾漢奸、《放下你的鞭子》 飾老漢、《把眼光放遠一點》飾老大、《前線》飾主角哥洛夫。擔任舞台布景設計的戲劇:《日出》(36年)、《威尼斯商人》(36年)、《鍍金》(36年)。
其他作品
《中華女兒》(與翟強合作)
《母親》
《深山裏的菊花》
《紅旗譜》
《駱駝祥子》
《邊城》
《春桃》
《狂》
本文到此結束,希望對大家有所幫助呢。

 微信扫一扫打赏
微信扫一扫打赏